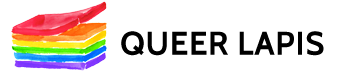不是为了好玩才做:Queer Lapis 性工作者系列第三部
文/Vinodh Pillai | 23 Dec, 202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影响很多领取日薪工人的生计,性工作者也难以幸免。
莫哈末(非真实姓名),是Queer Lapis本系列其中一个受访的性工作者,三月迄今他只见了一个客户。为了应付生活,他被迫从事不同的临时工作,例如在饮食档口工作或當促销员。他的另外一个朋友诺丁(Nordin),也是一名男性工作者,因为还有正职,所以还能应付生活。
无论如何,诺丁指出,他认识很多性工作者,他们多数在巴生河流域,生活也不太好。诺丁指出,一名跨性别女子必须暂时停止提供性服务。
“其中一个跨性别女子停止提供性服务,她想要提供上门性服务,不过因为行管令的限制招徕客人并不容易,这的确影响了很多人,所幸有些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
通过艾滋病社群项目的努力,一些他们可以触及的性工作者在行管领期间得到援助,但非政府组织是否能够触及所有性工作者?
标签的问题
基于群众对性工作者长期的负面观感以及污名化,他们很多人必须隐姓埋名或保持低调,这使联系他们或为他们谋取权利的工作。也让很多非政府组织例如PT 基金会(PT Foundation)的计划面对重重障碍,尤其在为性工作者提供艾滋病毒或艾滋病教育以及支援的工作上。
PT基金会的代理营运总监戴雷蒙(译名)认为将性工作者标签为妓女或污秽,让公众建立永久性的印象:即性工作者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投身性工作的目的等。这让公众很难接受有些人安于从事性工作。例如,一些人或许一开始因环境所逼,迫切需要钱而投身性工作, 但日子久了,他们可以自力更生,展开了自己的性工作者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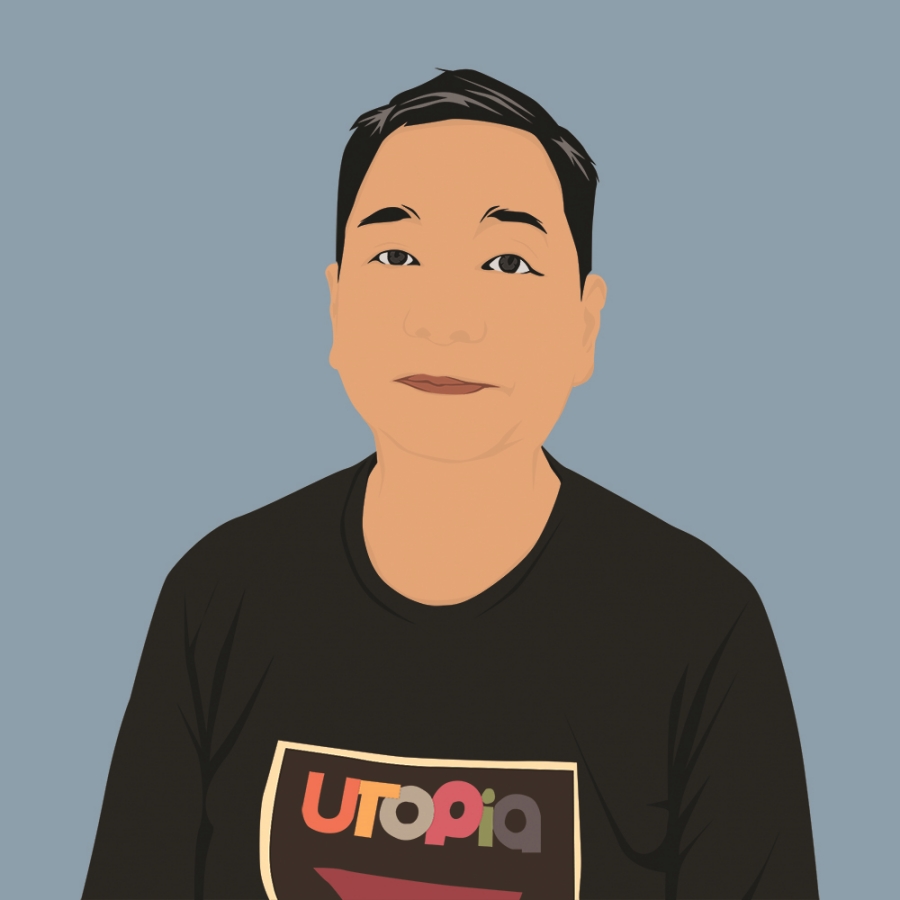
这些负面印象导致性工作者不容易被联系,也致使录取性工作者成为权利推广者的工作有难度。对于很多艾滋病毒组织,有该社群的成员进行推广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了解相关的议题,也容易跟客户建立互信。
雷蒙说,“在我于这个领域工作的日子里,我只认识两个人可以很自在地说,‘我是一个女性性工作者同时从事性工作者的权利推广工作’。所以概括而言,污名化非常严重,即便是在这个社群当中,理应安全的环境——很少人愿意从事这类工作,男性性工作者就更不用说了。”
当中少数成为性工作者权利推广人员就是31岁的杰克。青少年后期,杰克曾从事性工作长达六个月。一个尝试要缴付升学费用的离家少年,他在吉隆坡当地一间按摩院担任按摩男孩,轻易地找到了一笔块钱。他与同事为客户提供按摩或性服务,酬劳就是额外的现金。他记得当时也有一些外籍人士共事,很多都是为了赚取快钱以便能汇钱回家让家乡的家人无需三餐不继。
杰克解释说:“本地人,多数是因为被家人赶出来,他们孤苦无依,无处可去也没有机会和技能做出自己想要的改变——他们也可能拥有相关的技能,但赚取的酬劳不比在这里赚的多。”
他补充说,这也是为何他多数的前同事时至今日仍在提供性服务,15年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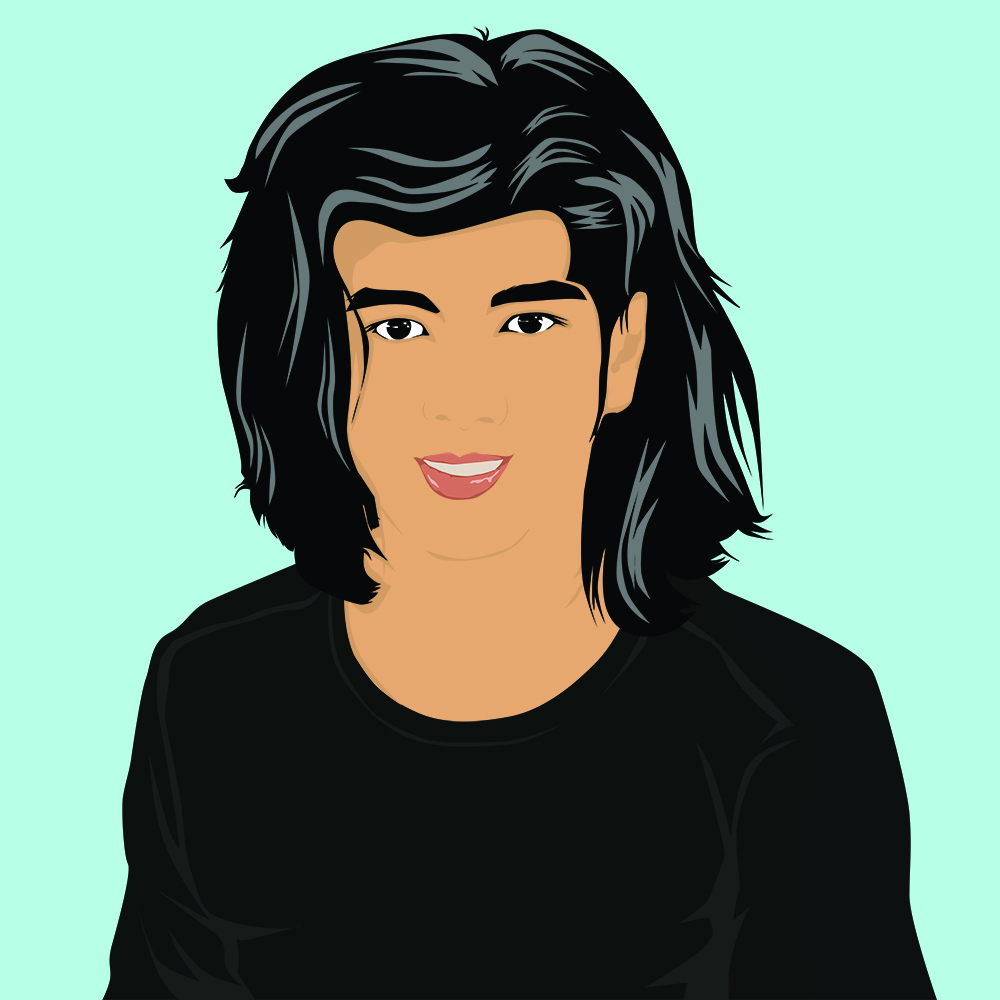
基于性取向被赶出家门或遭家人排挤,对于安身之处或生计毫无头绪,这些对于马来西亚LGBTQ+人士来说非常地普遍。对于很多性工作者而言,这就是他们入行的原因。
杰克不久之后曾担任好一阵子客服人员,但工作前途有限,让他非常沮丧。后来获PT基金会录取成为社群推广人员后,他在工作上找到了意义以及看到未来。“这个社群常被排挤,一些人士甚至政策都被忽视。但作为这个社群的一份子,我们要靠自己为未来创造有意义的改变。”
信用赤字
身份认同是LGBTQ+的性工作者遭受多重污名化——他们是性工作者,是LGBTQ+也可能穷困潦倒,这让他们在寻求医疗服务的时候,产生不信任以及恐惧。很多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感受无可厚非。
LGBTQ+社群当中,跨性别女子因与性工作挂钩而遭受更多污名化。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投诉遭受医务人员的歧视对待,让他们一再拖延至为时已晚才寻求治疗,直接否定他们接受无差别医疗服务的权利。
前性工作者以及现任跨性别权利推广分子嘉蒂尼(Khartini Slamah),或更常被称为蒂尼姐,相信这与前政府针对艾滋病毒或艾滋病的推广用词相关,很多人因此依然惧怕性工作者,预设如果他们不采取安全性行为,感染病毒的风险更高。
蒂尼姐说:“即便90年代或00年代,人们还是很惧怕跨性别性工作者,我们这些跨性别性工作者都担心,因为马来西亚社会一般上都对艾滋病毒携带者有偏见。她提及政府所谓的“恐吓手段”如何让性工作者对艾滋病毒或性病检验敬而远之。

为此,蒂尼姐抨击早期那些动辄就评断人的医生以及护士,他们会无礼对待跨性别病人或拒绝治疗他们。他责怪他们,并认为他们需要为了一些跨性别朋友感染艾滋病而负责;当时他们太害怕,根本不敢去检测,所以一直不知道自己感染病毒。幸好,时代变了。
“因为诊所里的社工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推广以及介入,越来越多跨性别人士愿意接受治疗,医生也变得更敏感。就算他们看到是跨性别病人来求诊,他们不会询问你的历史、性工作等……”她补充,“我觉得很多年轻的MSM(与男人发生性行为的男人)开始站出来。”
但要求性工作者信任或依赖公机构甚至政府,都比较强人所难。
雷蒙说:“我不认为他们当中有人会去向政府披露自己是性工作者,询问政府可以如何协助他们。”
“他们会说自己是来自B40(低收入)群组,需要政府补贴,但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是性工作者。”
杰克指出,性工作者为了避免被地方单位骚扰的可能性,在寻求医疗服务的时候不会承认自己是性工作者。雷蒙以及杰克都认为州政府机构是性工作者寻求协助的最后选择。针对性工作者以及LGBTQ+人士的各种法律条文,可能让他们觉得所有政府官员会一样歧视以及负面对待他们。
‘性工作者权利被剥夺’
莫哈末了解自己从事非法的工作,因为马来西亚极具争议性的肛交法律条文,将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定为刑事罪行。

被短时间可以赚取很多钱的说法吸引,莫哈末18岁那年涉猎性工作。四年的全职性工作让他攒了足够的钱,但过程一点都不容易。雪上加霜,目前半工读以及从事性工作者的莫哈末,是一名穆斯林。这意味着如果他被宗教组织逮捕,除了警方以及民事法庭,他将在州伊斯兰法下被提控。
他苦涩地追述一次在性派对上被逮捕的经验,他说,宗教执法官员以欺凌的手段迫使他悔过。
“他们一些可以接受我们(从事性工作),不过一些不能接受,所以很多被宗教局施压过的性工作者都患上忧郁症。”
他说:“对我而言,马来西亚性工作者的权利已经被限制了。我们这样的人,很难从事我们的工作,或通过我们想要的方式赚钱。也有太多的障碍阻止我们像普通人一样争取我们的权利。”
另一边,莫哈末的朋友,诺丁,一个非二元性别性工作者也曾几次被逮捕。他追述说,其中几次,他因为‘变装’而被逮捕,还有一次,因为给客户提供口交服务而被警方索贿。两次的际遇让他认为,伊斯兰法将LGBTQ+的现实人生刑事化,根本不合理。
“他们援引不止一条法律来提控,有很多罪名,尤其在伊斯兰法律当中。我觉得,他们有一些条文将在任何地方进行不正当的行为……干扰公众(不正当的行为扰民)。这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这不好——这让很多人转入地下活动,他们害怕面对外面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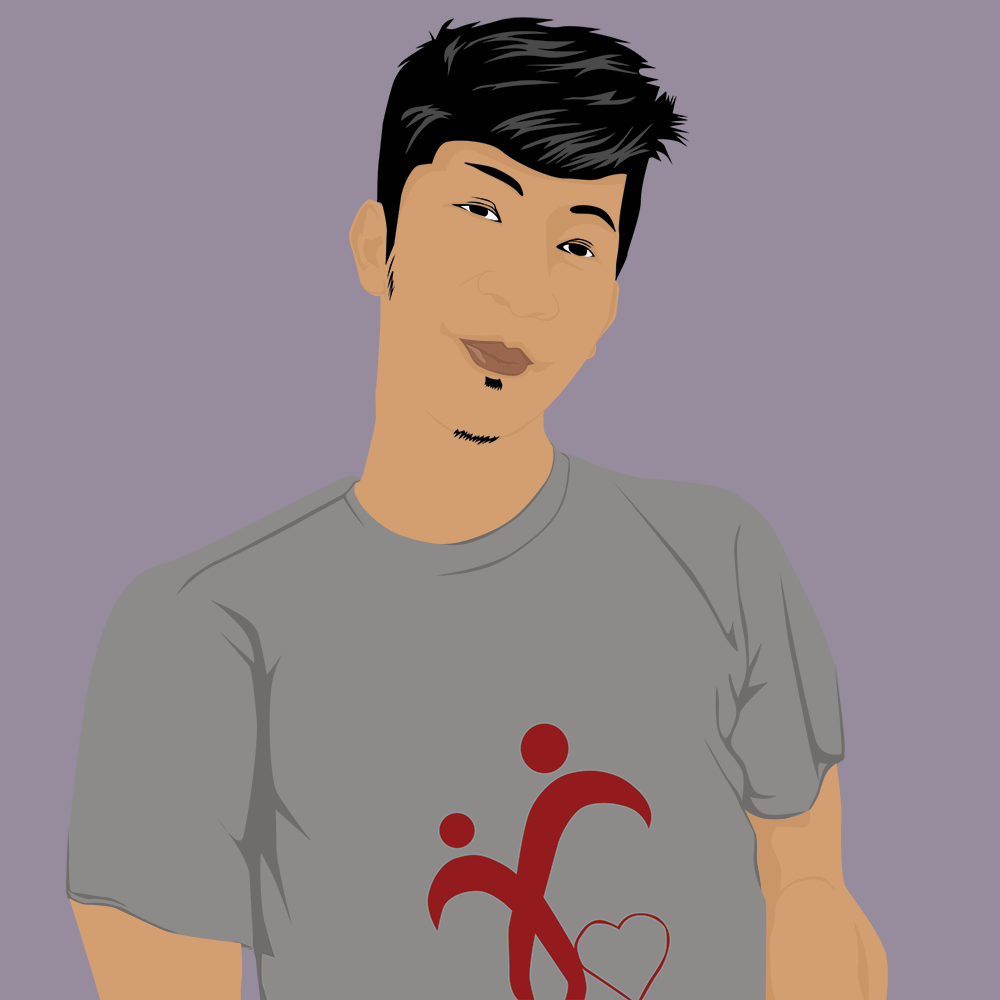
他补充说,这不公平,性工作者应该有工作的权利,法律或执法单位不应威胁到他们的权利。他认为,这些法律并未考虑到性工作者投入这个行业的理由,例如诺丁,他因为需要钱升学才投入性工作。
“我们有权利继续从事性工作,我们有我们的理由。不过,人们不喜欢聆听我们的理由。他们认为我们是因为好玩……随意从事这分工作。不过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们需要这分工作,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对于那些没有相同经历的人,他们不会了解。”
*
留守我们的最终章——对于性工作的常见问答以及可以协助性工作者的法律以及社会资源。
阅读我们性工作系列其他文章。
~ ~ ~ ~ ~ ~
Vinodh Pillai 是一名LGBTQ+议题作者
本项目是Vinodh Pillai, Queer Lapis 以及 Projek Dialog 的合作项目。
插图:Art.Zaid
编辑:冯启德,Thilaga, Ryan Ong, Lee Jia Chze 以及 Soo Kin Y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