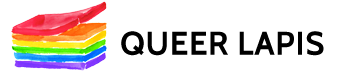独立广场到牢狱: Queer Lapis 性工作者系列 第一部
文/VINODH PILLAI | Nov 27, 2020

“育有7子女母亲 家中唯一收入支柱被控卖淫”。
“淫窟被捣破 22人隆扫荡行动被捕”。
“女子在白沙罗公寓提供性服务被捕”。
近日这三宗就性工作者被逮捕的媒体报道在马来西亚简直司空见惯。而且,在我国以卖淫为目的招客的行为属违法,难怪性工作者总是恶名昭彰。
这些污名化头条背后有哪些人性故事?性工作者的故事又是如何?与性工作者,性工作者权利推广分子、律师以及社运分子对话,Queer Lapis诚邀您聆听常被媒体边缘化、被历史遗忘的马来西亚性工作者的写实人生。这是Queer Lapis 性工作者系列四部曲的第一部。
从前与现在的性工作
60年代的性工作者,一个晚上辛苦耕耘回家后身上有千多令吉现金并非难事——至少根据前性工作者嘉蒂尼诗拉玛(Khartini Slamah),人称蒂尼姐(Kak Tini)的说辞。她说,性工作者当年都在妓院模式的卖淫场所、又或在臭名远播的秋杰路,即吉隆坡市中心那一带讨生活,那里是性工作者的“天堂”。
“从前,我们会到独立广场或九龙,当时我们是这样叫的,东姑阿都拉曼路附近的环球(布店)后方,之前那里的停车场、戏院后方,在那里还没有戏院之前,当然还有秋杰后巷。当时,这是我们远近驰名的赚钱场所,更早期,还有武吉免登,就是希尔顿区。”
听着蒂尼姐娓娓道来,如今她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跨性别以及性工作者权利推广分子。
收费以及客源因地点而异。例如,那些在后巷工作的性工作者向每个客户收费70令吉, 而那些陪侍的价格则介于每人100到200令吉。那些光顾独立广场的客人则会开车到场,收费也因人而异。这是顺性别男性工作者以及女性工作者运作的方式。如今的作业形式也大同小异。
苏薇(Selvi)推动女性工作者权益超过20年,她追溯90年代初期的性工作,较为普遍且不多限制——性工作者可以安心工作,虽然有关当局偶尔会进行突击活动。随着突击及扫荡活动与日俱增,很多性工作者开始在网上接活,如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交友应用程式以及即时聊天应用程式来推广自己的服务。

当时涉及性工作领域的多数是外籍劳工(不是说本地人不从事性工作),不过现在更多本地人从事性工作。在2018年,卫生部估计马来西亚有2万2000名女子性工作者,但却没有以国籍分类,不过2010年的一份未发布的报告指出性工作者的人数达6万人,其中2万人是女性跨性别者。
苏薇说:“最近,我跟朋友一起去,他说村子里,还有人做,他们是青少年,14-15岁。因为他们使用手机,(他们)要求外籍劳工帮他们的电话充值,之后就可以展示自己的身体,私处,或任何部位,他们都是这样做的。他们还在做。我知道性工作者都会尽量低调,不公诸于世。但这是一个社群,人家会知道谁是性工作者。”
蒂尼姐和苏薇都观察到性工作者开始离开城市地区。因为担心被逮捕,他们居无定所,这让蒂尼姐这些社运分子在安排他们进行性病或艾滋病毒测试上面对很大的挑战。为了避开当局的耳目,他们会迁移到另外一个州属或国家。
导致性工作者流动的原因包括不断涌入本地的外籍性工作者。有大批来自泰南以及印尼的性工作者流入马来西亚,因为他们能说马来文,客户可能会认为他们来自吉打或槟城,这对本地的性工作者来说是强劲的竞争。如果他们是外籍人士且从事性工作被逮捕,就是罪上加罪。他们必须掏出很多钱来检测或治疗性病或艾滋病,同时还要面对被遣送回国的风险。
扫荡、逮捕以及‘遏止’性工作
表面上,上网招客看来比较安全,但性工作者还是担心近年来激增的扫荡以及突击行动。在马来西亚,为卖淫招徕客户是刑事罪,可被判坐牢刑期高达一年、罚款或两者兼施。
女性性工作者多数是在红灯区循例行动时被警方逮捕,而跨性别女性则多数会因为被怀疑卖淫或“变装”而被逮捕,”变装”抵触了法律,包括抵触一些州属的伊斯兰法 (马来西亚实施双轨法律制度,即民事以及伊斯兰法)。
蒂尼姐依然记得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初期,很多人不懂自己的权利,他们会认罪然后缴付罚款了事,他们不会挑战被逮捕的事实。据说,他们当中有人被威胁若不认罪就会被监禁。有关当局也以宗教之名要他们认罪,将性工作标签为罪孽。
“当然,跨性别女子早期都尝试避开被扣留在拘留所的命运,我们跟男人会被关在一起,如果你有乳房,那些男人就会性侵你。但你要怎样举报自己被性侵?你的身份证上是个男人……”马来西亚法律下,强奸被定义为在违反女子个人意愿或在未经她的许可下,与一名女子发生性关系。这些法律条文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并不中立,也无保障其他人免于性侵或强奸。因为国家不允许法定社会性别认证,让遭受性暴力的跨性别女子诉诸公义的途径更为艰巨。

所以当她在“与男人发生性行为的男人“社区的非营利组织粉红三角(Pink Triangle)(如今PT 基金会(PT Foundation))工作时,她尝试教育警方不要将顺性别男子与跨性别女子拘留或囚禁在同一个扣留所或监狱里,偶尔她的教育工作会取得一些成果。
跨性别性工作者社群的待遇虽有大大的改善,但这还是一场很漫长的斗争。蒂尼姐希望警察部队成员,或其他领域,例如医疗领域的从业员,在入行的初期就可以被培训的更敏感,更可以了解跨性别性工作者面对的现实挑战,这个议题不仅限于艾滋病毒或艾滋病,这是人权框架里的议题。
蒂尼姐问说:“他们常说,’你不从事性工作就得了‘, 行,那如果性工作者是在扫荡行动中被逮捕,被迫停工,如何?”, “如果他是单亲妈妈?如果她坐牢了,她的孩子怎么办?他们没有思考过这些,这不是一个全面性的策略,一味呼吁大家停止从事性工作……”
她补充说:“你必须明白性工作者的文化——如果你已经习惯每天都有钱花,突然间,打个比方,你到工厂,工作一个月,差别太大了。你每天都需要用钱,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存款。不是所有性工作者都有存款,我赚了很多钱,但我不擅长理财还有存钱,并没有为未来规划。”
蒂尼姐希望相关当局不要推动一些不切实际的措施。她指出,必须在培训、技术以及能力培养之后,才能更实在地期许性工作者能够转行从事其他工作。
本地以及外地人
男性性工作者的动机也很雷同,根据PT基金会十年前的调查显示,早期他们多数是想要赚更多外快的外籍人士。这些男人年龄介于20多岁或30岁出一点,他们来自邻近的区域例如泰国、印尼、缅甸、越南或菲律宾,有些甚至远自香港或中国。但他们不会逗留太久,通常持社交入境签证。
PT基金会的代营运总监戴雷蒙(译名)解释说:“他们每趟逗留一个月,争取在逗留期间赚取至少足够应付开销的收入,如果他们有额外的收入,就算是赚到,然后他们可能就去新加坡或台湾等其他国家。”
“可以赚大钱的地方是新加坡、香港这些主要城市,之后当然是吉隆坡或雅加达这些大城市——这些拥有购买能力的地方。”
PT基金会供内部参考以及未曾发布的研究显示男性工作者以按摩院为基地,过去这里长期跟性工作挂钩。这些提供按摩服务的男子符合了既定印象,即有魅力、年轻、面貌姣好的同志肌肉男。戴雷蒙说,取决于客户光顾的场所,一些地方提供的‘额外’服务可能会比另一些地方来的更露骨。
他补充说:“很多时候,业者会针对按摩服务向客人收费,但在房里,客户跟提供按摩服务的男子可以私下协商, 于是,业者提供非常少的基本收入,因为这些按摩的男子要通过客户直接给他们的小费来补贴收入上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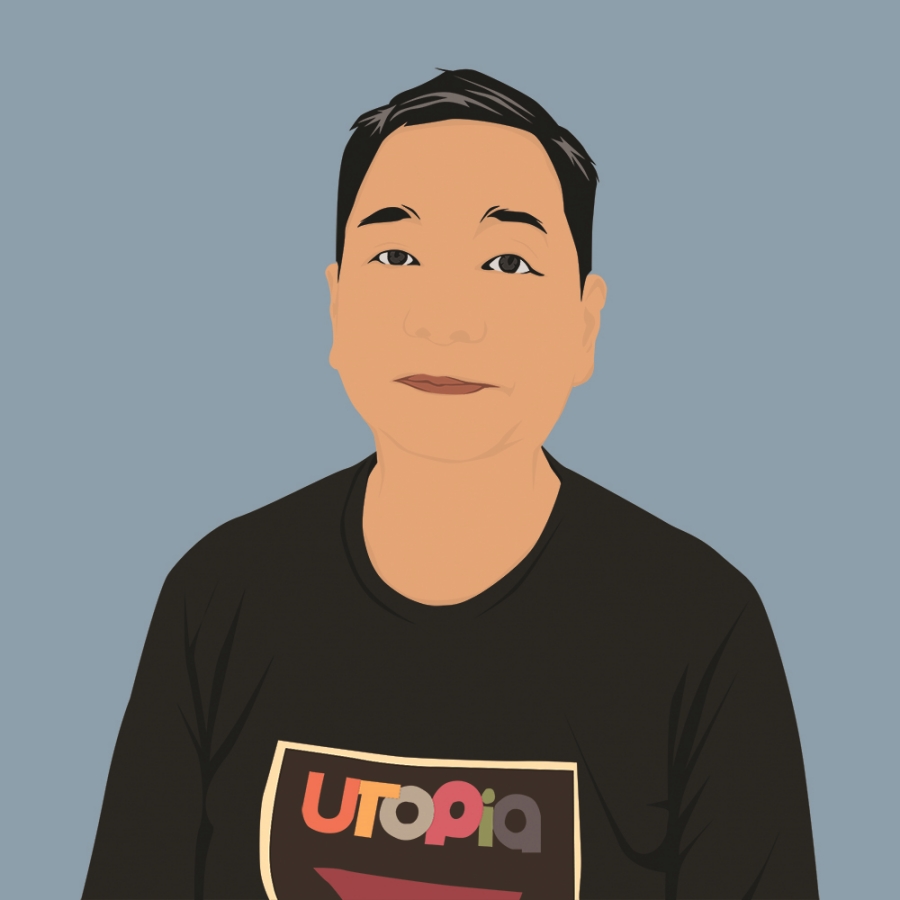
当时,没有很多本地男子从事性工作,不过,客人与性工作者之间的权力格局却极为显著:年轻男性会为了高级的晚餐、酒店设备或出国的机会,而专找比较年长的外国男人。他们提供所谓的‘陪侍服务‘, 这通常会包括性服务,虽然一般上不会展示在他们网上的个人简介。但通常在简介里出现“我在寻找伴游”的字眼,就能让人明白他们是在提供或寻找性服务。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本地男性工作者。蒂尼姐回想起曾见过一些穿着时尚的的年轻“鱼仔”(小鱼,别名糖宝)或者“小白脸”,他们手持最新的科技产品,穿戴最时尚的服装在吉隆坡市政厅大厦附近讨生活。正如女性以及跨性别工作者,他们的客户群也不同,一些目标瞄准已婚女性或名人显要的妻子。
“不过,当时也有年轻男子性工作者并不符合市场的胃口,所以他们就会接受任何客人,包括男人或任何人,只为了钱。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所以他们不理解性工作者这个名词……一旦有人问他们是不是性工作者,他们不会承认。所以最好就只是叫他们的名字…….你根本不用问。有的人很公开,有的人则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被标签或被归纳为性工作者的类别。”
但谁可以责怪他们?
苏薇说,“没人愿意以性工作者自居,因为他们担心被社会排挤或被逮捕。”苏薇期许有一天所有的性工作者、男或女或跨性别性工作者可以联手走出来。
她说,在马来西亚如果要捍卫性工作者的权利,不能孤军作战。
*
阅读我们性工作系列其他文章。
女子性工作者、男子性工作者或跨性别性工作者可以联手捍卫自己的权益吗?留守下一个章节以便了解性工作者在被逮捕之后的遭遇、性工作者权利推广分子奋斗的目标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挑战。
~ ~ ~ ~ ~ ~
Vinodh Pillai 是一名LGBTQ+议题作者
本项目是Vinodh Pillai, Queer Lapis 以及 Projek Dialog 的合作项目。
插图:Art.Zaid
编辑:冯启德,Thilaga, Ryan Ong, Lee Jia Chze 以及 Soo Kin Yong